冯建荣秦会稽刻石考论
(一)
中华从来多名山,会稽自昔独灿烂。
早在年前,孔子就对会稽山的具体方位作了认定。“吴伐越,堕会稽……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1这段史料中,同时出现了越、会稽、会稽之山、禹、防风氏等地名、山名、人名,说明了会稽山就在今之浙江绍兴。《嘉泰会稽志》则进一步指明:“会稽山在(会稽)县东南一十二里”2。
会稽山最初位列九大名山之首。《周礼》以东南、正南、河南、正东、河东、正西、东北、河内、正北为序,排列九州、九山,指出“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3。何谓九山?《吕氏春秋》有云:“会稽、太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4
会稽山曾被排名四大镇山之先。“四镇,山之重大者,谓扬州之会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之医巫闾山,冀州之霍山”5。
会稽山早就受到华夏先祖的尊崇。相传黄帝时,尝于此建馆遗谶。“龙瑞宫在(会稽)县东南二十五里,有禹穴及阳明洞天。道家以为黄帝时尝建侯神馆于此”6。“《吴越春秋》称,覆釜山之中,有金简玉字之书,黄帝之遗谶也”7。舜在会稽留下了“上虞”、“百官”之地名典故8,以及舜江、舜田、舜井等历史遗迹,后世屡建“舜王庙”、“大舜庙”以志纪念。而大禹之与会稽山,更是渊源可薮:“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9,“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10,“禹封泰山,禅会稽”11,“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12,“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13。
黄帝、舜、禹,是华夏的始祖、先祖,他们都与会稽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作为我国第一个王朝奠基者的大禹,会稽更是他的治水毕竟之所,地平天成之处。由此看来,会稽山称得上是一座祖山,“是一座镇山、尊山,是一座神山”14,更是一座开创了中国王朝历史的名山。
(二)会稽山上之大禹像
“稽山形胜郁岧峣,南镇封坛世代遥。”15会稽山的祭祀敕封活动有着久远历史。
最早祭禹的,可以追溯到夏王启派遣的使者及禹之后人。“启使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庙于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16,以守禹冢。
“最早祭祀会稽山神的是越王勾践”17。当年文种向勾践献“灭吴九术”,第一术为“尊天事鬼,以求其福”。对此,“越王曰:‘善。’”于是乎,“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祭陵山于会稽,祀水泽于江州”18。
最早亲祭大禹的帝王是秦始皇。关于秦始皇南巡会稽祭大禹等情况,文献多有记载。“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19。“三十七年(前)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20。秦始皇“三十七年,东游之会稽……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適(通“谪”)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21。“乌程、余杭、黝、歙、无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帝刻石徙之”22。“秦始皇发会稽適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县相属”23。“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24。
为说明问题,这里不妨再引录些有关越人性情方面的记述。越王勾践曾对孔子喟叹:“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25“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朝服于楚”26。“齐庄子请攻越,问于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遗令曰:无攻越,越,猛虎也。’”27墨子亦云:“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28看来,越人骨子里确实是强悍好胜,不易臣服的。
(三)
秦始皇
现在再回到秦始皇南巡会稽这件事情上来。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酷爱出巡的帝王之一。从公元前年开始,在他近四分之一的皇帝生涯中,八次长途跋涉,“亲巡天下,周览远方”,忙碌地奔波于遍布全国的“驰道”29上。从以上引录的诸多文献来分析,秦始皇不顾万里之遥、舟车劳顿,不惧水波之恶、风雨严寒,以会稽作为此次出巡的最终目的地,有着十分明确的目的性。概而言之,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第一,祭拜大禹,以示大统。
秦始皇对虞舜,是于九嶷山“望祀”;而对大禹,则是“上会稽”亲祭,足见大禹在其心目中的巨大影响和崇高地位。秦始皇“上会稽”,登的是越地的主要山峰,由此绍兴有了“秦望山”等山名;望的是秦中的大好河山,于是又有了“望秦山”等山名。
大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夏王朝的奠基者,也是华夏民族最基本、最一致的文化认同者之一。秦始皇亲临大禹葬地,亲祭大禹之灵,显然是为了彰显自己一统天下的雄才大略,更是为了表明自己君临天下的正统地位。
第二,歌颂秦德,弘扬秦风。
这尤其可以从刻石内容中得以证实。《史记》记载秦始皇出巡时所立刻石,共有九块。分别为始皇二十八年(前)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之罘刻石》和《琅琊台刻石》;始皇二十九年(前)的《之罘刻石》和《之罘东观刻石》;始皇三十二年(前)的《碣石门刻石》;始皇三十五年(前)的《东海上朐界刻石》;始皇三十七年(前)的《会稽刻石》30。其中六块刻石的内容为《史记》全文收录。这些刻石,历经浩劫,或被人为破坏,或漶泐于岁月,或烬毁于野火,仅《泰山刻石》与《琅琊台刻石》尚存片鳞鸿爪,余皆荡然无存。
但是,我们依然可从文献记载和残碑断字中捕捉其主要内容:一是记述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历史背景、征战历程和不朽功绩;二是记述秦始皇治理天下的大政方针、主要举措和巨大成效;三是记述立石的直接动因——群臣力请。如《会稽刻石》中写道:“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始定刑名”,“初平法式”,“贵贱并通”,“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31。
第三,恩威越人,稳定越地。
如果说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立刻石、移风俗,是对越人施恩怀柔、颂扬皇恩浩荡的话,那么在“示强”越地、“威服”越人方面,则显示了巨大的皇权威力,颇有震慑作用。秦始皇治越主要举措有五:一是将部分越人强制迁徙至今皖南、浙西地区;二是将天下待罪遣戍的官吏和百姓,放逐至钱塘江以南原大越之地;三是将大越易名为山阴;四是眺望南海,防备“滨于江南海上”的东海外越人的反抗;五是着令遣戍越人开凿“陵水道”运河。其中,最为严酷的要数“迁徙”、“適遣”之举。始皇二十六年(前),“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以適遣戍”;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三十五年,“益发適徙边”32。这些史料表明,通过適徙来改变民族构成、融合民族文化,是秦始皇巩固一统天下局面的十分重要的措施。
秦始皇采取的这几项十分严酷的措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那就是镇压越地的“天子气”,改变越人“好战”、“猛虎”、“脆而愚”、“锐兵任死”之“常性”。想必秦始皇对越王勾践当年卧薪尝胆、报仇雪耻之作为,心存畏惧;对自己亲历的,在“降越君”33和服瓯越、南越、闽越等“勾践之裔”34聚居地区过程中的异常艰辛,更是耿耿于怀。诚如陈桥驿先生所分析的那样:“秦始皇敉平东南地区,由于防止强悍的越人反抗,除了驱赶和强迫这地区的越人迁移以外,又把勾践的故都大越改为山阴,在吴越旧址建置会稽郡,郡治置于吴,很有不再称这个地为‘越’的心愿。”35
(四)
秦始皇频频出巡,包括亲临会稽,固然是为着巩固中央集权统治,使自己开创的伟业“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36。但是,客观地讲,这对于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37和“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38等统一举措,巩固一统天下的局面,是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的。他作为“江南运河的创始人”39,在“百尺渎”、“吴古故水道”等春秋时期开凿的运河及太湖流域原有自然河道的基础上,“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40,为后来的京杭大运河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而大运河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和现实作用是自不待言的。
秦始皇确实无愧为“千古一帝”。他统治天下的制度典章,在“汉承秦制”的基础上,为后世继承和发扬。他一统天下的丰功伟绩,值得人们永远缅怀。据说,英语的中国一词“China”,最初是从罗马语“Chin”(秦)演变过来的,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大秦帝国对于世界的影响。
峨嵋山又称刻石山、鹅鼻山
年9月23日,星期六,秋高气爽,我与章生建、高新华、邢玉清等君一起,去绍兴县平水镇岔路口村的峨嵋山(又称鹅鼻山)自然村访问,并在黄锡云、汤金尧、陈刚、孙其康、尉瑞庆、郦校根、郦朝根诸君的陪同下,从这一方向登上刻石山,有感而发,作《忆秦皇》:
刻石山上览九州,李斯碑里写春秋。棋盘石中定乾坤,三十六郡统宇宙。
遥想秦皇当年,雄视天下,并吞六国,观东海,上会稽,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壮怀激烈,踌躇满志。
次年10月5日,国庆假日,我又与孙君、王张泉、王彪诸君一起,自绍兴县兰亭镇大庆村方向再登此山,作《重上刻石山》:
荆棘丛生行路难,殊途同归信可叹。一览并非众山小,只缘山外更有山。
中华民族大家庭,巩固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是在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基础上,巩固发展繁荣起来的。千秋伟业,继往开来;斯情斯景,未免使人感慨万千。
然而,历史车轮的行进,往往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好的心愿,如果不辅之以好的方法,常常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方法得当,事半功倍。方法失当,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历史常常会嘲弄一厢情愿的人。对于秦始皇而言,“焚书坑儒”41,不读孔子的《论语》,不懂得“过犹不及”42的道理,似乎情有可原;但是,不读相国、“仲父”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不接受“物极必反”43的提醒,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历史对秦始皇的嘲弄,首先是在他离开会稽,“并海上”,“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并于七月“崩于沙丘平台”44,匆匆谢世。更为惨烈的是,在他离世一周年之际,即二世元年七月(前),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反秦起义;九月,起义即在他最放心不下的会稽得到了响应,那位避事越地,曾在秦始皇巡视会稽时放言“彼可取而代也”45,“长八尺余,力能杠鼎,才气过人”46的楚国将门之后项羽,与他叔父项梁一起,毅然揭竿而起,加入了反秦的队伍,并在亡秦战争中立下了头功。秦始皇当年的忧虑,可谓是先见之明。后来的事实是,越人果然在亡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越王无彊“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为了褒奖越人,“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47。
会稽刻石
(五)
有了上面这样一些铺垫,现在就可以集中来谈谈《会稽刻石》的重要作用和伟大意义了。
第一,《会稽刻石》成就了越地的第一美文。
刻石正文为四言韵文,三句一韵,共24韵节,计字,较《史记》所记少一字。其文字凝练、隽永,文风庄重、典雅,文思畅达、井然,易解易记,是难得的好铭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堪称古越大地上诞生的第一篇美文。“那言简意赅、含蓄流畅的文辞,词藻华丽、琅琅上口的韵文……无不显示出它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艺术瑰宝”48。
五百六十多年后,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于“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暮春之初”,在“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会稽山阴之兰亭”,写下的千古绝唱《兰亭集序》,无疑是诞生在古越大地上的又一篇美文。《会稽刻石》与《兰亭集序》,文辞宛若天成,堪称文章“双绝”;书艺精美绝伦,堪称书法“双绝”;文辞与书艺珠联璧合,堪称文、书“双绝”。这是越乡人民的骄傲,也是民族文化的华章。“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想必王羲之醉意微浓、思绪翩跹、兴笔挥毫《兰亭集序》时,是联想到了昔之《会稽刻石》的。“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果然,王羲之言中了。
第二,《会稽刻石》宣省了越人的风俗习性。
管子当年曾以所见所闻,称“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49。勾践自称越人脆愚、任死,其地乃“僻陋之邦”,其民乃“蛮夷之民”50。“相传越俗自勾践时起,男女间关系不严”51,“教化习俗还很落后,氏族社会偶婚制习俗尚未清除”52,“当其时盖欲民之多,而不复禁其淫泆。传至六国之末,而其风犹在”53。越人“争立”、“好战”、“猛虎”、“断发文身”54,“处危争死”55,“三弑其君”56。这些记述,大体上反映了当时越地的环境与民风。而《会稽刻石》三分之一的铭文内容,正是针对这些情况的,这也是此刻石与《史记》收录的其他五块刻石内容的最大不同之所在。
《会稽刻石》的第三韵,即宣告秦始皇“逐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齐壮”57之意图。第十六韵迄第二十三韵,此八韵所述均为荡涤旧习,开启新风之事:“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58越地从最初的荒服之地,发展为后来的名人辈出、文化灿烂的斯文之乡,不可否认确实是与最初宣省的这种民风习俗长期以来的潜移默化紧密相关。即使在今天读来,诸如“男女洁诚”、“男秉义程”、“咸化廉清”、“大治濯俗”、“皆遵度轨”、“和安敦勉”等思想,仍然具有积极的教化意义。
《会稽刻石》留传至今,可谓历经磨难,来之不易。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立石刻颂秦德”、秦二世元年(前)“尽刻始皇所立刻石”,至唐开元二十四年(),《会稽刻石》经历千年风雨,仍岿然屹立,这从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所云“其碑见在会稽山上”得以印证。而从北宋初欧阳修、北宋末赵明诚分辑《集古录》、《金石录》时,均未见录《会稽刻石》来分析,刻石可能于北宋早期即遭毁佚。南宋地方志有载,此石“宜在此山”59,陆游亦有“残碑不禁野火燎,造物似报焚书虐”60的诗句,皆可佐证。元至正元年()五月,绍兴路推官申屠駉,据家藏旧拓本重新摹刻,并题记于后,与按徐铉摹本所刻的《峄山刻石》互为表里,置于会稽黉舍。清康熙年间(—),碑文被人磨去。乾隆五十七年()四月,绍兴知府李亨特再据申屠氏本复刻于原石,并以自跋代原跋;七月,翁方纲补刻短跋。嘉庆元年()、二年,又分别勒记阮元、陈焯题名。年,刻石移置会稽山大禹陵内之碑廊,置屏壁以永久保护。《会稽刻石》历经了漫长曲折的两千多年,屡遭磨灭,几经摹刻,然其灵魂精髓却始终浑朴如一。我们从这段历史中可以感受到,越人对《会稽刻石》是引以为荣和呵护珍爱的,而有了这份自豪与珍爱,自然也就多了一分接受宣省的自觉。大禹陵内的会稽刻石拓片
第三,《会稽刻石》树立了我国的书艺丰碑。
汉字到了秦代,产生了两个历史性飞跃:一是书写字体的规范划一,如“小篆”,意味着秦对六国旧字体的整理;二是书法艺术开启了新风,如“隶书”,在一群无名无姓被共同称呼为“隶”的书写者手中被创造、被实验。而《会稽刻石》的撰文及书写者李斯61,无疑是其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他主创秦一统天下的文字“小篆”,被后世称为“小篆之祖”;他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知道姓名的书法家”62,“是书法史上有明确记载而且至今可以见到他的书法的最早书法家”63,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书碑名家”64。
作为书法艺术的丰碑,李斯小篆对后世的隶、楷、行、草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我们现在见到的《会稽刻石》经多个朝代重摹,或许有失原刻风貌,但其书体依然清劲圆润,明晰端正,法度谨严,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感受两千年前的辉煌书艺,领略一代大家的书法神韵。正如我们虽然无法触摸《兰亭集序》的真迹,但还是能从历代临摹作品中一睹书圣独领风骚的书艺。
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中,对李斯书法的评价是“世为冠盖,不易施平”。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说,“李君创法,神虑精微,铁为肢体,虬作骖騑,江海渺漫,山岳峨巍,长风万里,鸾凤于飞”,“画如铁石,字若飞动,作楷隶之祖,为不易之法”。唐李嗣真《书品后》中赞叹,“李斯小篆之精,古今妙绝……犹夫千钧强弩,万石洪钟”。宋刘跂《秦篆谱序》中说:“李斯小篆,古今所师。”明赵宦光《篆书指南》中,称“秦斯为古今宗匠……书法至此,无以加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称赞“相斯之笔画如铁石,体若飞动,为书家宗法”。鲁迅先生也称赞李斯的书法“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65。
由此看来,李斯的书法艺术的确是出神入化,超凡脱俗的,后世之人将其书碑奉为楷则,的确当之无愧。有了李斯与王羲之这样两位丰碑式的人物,将绍兴称为书法之乡,理所当然;将绍兴称为书法故乡,也未尝不可。
第四,《会稽刻石》流衍了神州的刻石之风。
“刻石之风流衍于秦汉之世”66。我们从《会稽刻石》和其他秦刻石中可以看到,秦刻石的形制与先秦相比,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尽管它们被称为刻石,但实际上与后来的碑已颇为相近了。这就表明:“秦刻石正处于春秋战国时期无一定形制的‘石’原始碑向后世有一定形制的碑转化的进程中,同时,这也有力地表明,刻石确实属于碑的范畴,是正在进化中的碑。”67正是在秦刻石的影响下,刻石文化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也由于《会稽刻石》之渊源,绍兴得开风气之先,在琳琅满目的刻石文化园里,大放异彩,美不胜收。清嘉庆年间,邑人杜春生辑《越中金石记》20卷,堪称越中金石集大成之作。其中,“辑存”考录碑版处,根据历代金石考和地方志载“阙访”处,共计处,足见越中金石之富,而埋于地下,弃于荒野,泯于岁时者,尤当难计其数。
有鉴于此,我年在绍兴县工作时,曾在强调开展田野调研,加强实地保护的同时,请有关方面对各类存世刻石进行捶拓,并以图录、释文的形式加以编纂出版。经过同仁们一年多时间的辛勤工作,终成《绍兴摩崖碑版集成》一书。中共绍兴县委原书记、今浙江省常务副省长陈敏尔同志欣然为本书题签。浙江省文物局长鲍贤伦同志拔冗终审。我亦为该书作序并向工作人员赠联。我在序言中写道,绍兴“摩崖题刻,琳琅满目,源远流第;碑版勒石,俯拾皆是,遐迩闻名”。这些石刻,“可补档案之不足,证文献之真缪,赏书法之多姿,知乡史之兴替,益后世之教化”。给工作人员的赠联是:“风餐露宿,搜拓空前绝后,泽被人物千载无穷;夙兴夜寐,考证劳师动众,惠同日月万世永恒。”
这本书图文并茂,收录了历史上山阴、会稽两县范围内字面基本完好,具有一定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摩崖94幅、碑版通、墓志20方,凡品。其中,东汉《大吉买山地记》,是迄今发现存世最早、面积最大的真实地券;留存于今宛委山之《龙瑞宫记》,系唐著名诗人、书法家贺知章之手迹;羊山石佛寺内题记,是新文化运动巨擘蔡元培先生的墨宝。此外,大禹陵之《岣嵝碑》,有学者新考证认为此系古越国祭南岳衡山的刻辞;兰亭的《鹅池碑》,传为书圣王羲之与王献之合书的“父子碑”;而兰亭的清康熙《临兰亭序碑》、乾隆《兰亭即事一律碑》,一石两面分刻御书,更是世所罕见的“祖孙碑”。这些碑刻,充分展示了越地文化品种之繁多、书法之精妙、史料之珍贵、内涵之丰富,足以令人仰止。
峄山刻石
第五,《会稽刻石》初成了独特的碑铭文体。
“从文体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史可视为各类文体孕育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也是各类文体之间相互作用,互相渗透,不断衍生出新品种的历史。正是这种经由多时代创作活动所引发的文学体类的自动和互动,促进了文学形式的创新、繁衍,并与它们所承载和表现的历史事件、作家情感等内容一起,共同构成缤纷复杂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史”68。碑铭文体,正是在秦代刻石文体的基础上成长发展起来的。
高利华等学者认为,“产生于越地的《会稽刻石》,不但标志着秦代刻石这种文体的成熟,已初步奠定碑铭文学的特征,而且对越地后来的文学氛围的形成产生了引导作用”。“秦统一后的刻石铭文在碑铭这一文体方面有开创价值”,“对碑铭体文学的形成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进而研究指出,“《会稽刻石》体现着碑体文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其叙事性”。“《会稽刻石》体现着碑体文的语言特点是文句整饬简洁,辞采雅训有则”。“《会稽刻石》体现着碑体文一个重要的特点便是颂的笔法,这是该文体与生俱来的特征”69。
通览《史记》收录的包括《会稽刻石》在内的六块刻石铭文,确实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内容,具有了“颂”的文体特征;其笔调,具有了“铭”的文体意义;其表现形式,具有了“碑”的文体模式。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秦刻石的艺术成就与文体创新,才迎来了入汉以后刻石文学的繁荣兴盛,才出现了东汉时期我国碑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才使得碑铭文体成为了汉代文学创作中与诗、赋一样重要的文体形式,以至最终出现了“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70的动人景象。
(六)
《秦〈会稽刻石〉考论》一书的编辑出版,缘起于年炎热的夏天发生的一场热烈的“百家争鸣”。这年的6月12日,《绍兴晚报》第4版发表了该报记者张兴刚先生采写的以《秦始皇会稽刻石碑的原址在哪?原碑该是个啥模样?》为长题的长篇整版文章,对刻石原址等问题,报道了颠覆性的观点,由此而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疑问。紧接着,9月6日、25日的《绍兴晚报》和9月29日、10月14日的《绍兴日报》又大篇幅地进行了相关报道。这样的报道与争鸣,自然有助于引发人们对于包括《会稽刻石》在内的弥足珍贵的绍兴文化遗产的更多北京市那家医院治白癜风好点滴型白癜风应注意
版权所有:Copyright © 2012-2020
云台山_云台天瀑

电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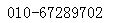
今天是:

